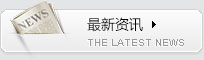邦达集团 BANGDA GROUP - 以科技为动力 以质量求生存
 首页> 新闻中心 > 公司动态
首页> 新闻中心 > 公司动态碑碣中的“淮阴城”历史
2018-09-10 11:14:39
2004年,由香港天马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《淮阴金石录》一书中,刊载了竖立在淮安老城府市口“淮阴市”碑的正、反两面照片。在说明文字中,这样写道:
此碑建于唐代,原立在淮阴故城中(即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),明时被移立于淮安府市口,后损坏,存放在楚州区勺湖公园内。时年,淮安府又仿制一块,现立于城内。
在这段话中,“淮阴故城”后用括号主观说明淮阴故城就在码头镇,而楚州区即指今淮安区。根据今存大量淮安历史文献、地方志、碑刻等记载,《淮阴金石录》一书所说,有失偏颇。
竖立于淮安城北门府市口的“淮阴市碑”
一、由“淮阴市”碑说起
首先,“淮阴市碑”并非唐碑。其碑身落款处有两个人名,皆为明代人。古人喜欢信而好古,不至于将珍贵唐碑磨平,再镌刻一块与原碑同样内容的碑。碑上两个落款的人名,一为“知府王廷器重修”,另一为“东鲁刘大文题”,虽都是明代人,但先后相差了100余年。
王廷器,名瑜,字廷器。宣德八年(1433)任都指挥佥事镇守淮安,充左副代陈瑄镇淮安督漕运,累进左军都督佥事。而刘大文是在150多年后的万历二十四年(1596)才来淮安担任淮安府知府。碑中,王廷器并未担任过知府,却署称“知府”,刘大文确是知府,却只泛泛署了自己的籍贯地“东鲁”。这是为何?一种说法是在宣德年间王廷器曾重修过此碑,而到了刘大文时,碑损重勒,并继续署上王廷器之名。刘大文署王廷器为知府,或许是因为王廷器镇守淮安时行使过知府的职能,也或者是古人的那种谦逊,才会有了这样一个题署方式。所以,磨唐碑刻新字之事更不可能发生。
其次,“淮阴市碑”并非从码头镇“移立”到府市口。据前文所示,碑中出现的两个人名都是明代人。一个是镇守淮安的“权官”,一个是淮安府的“父母官”,两个人的工作地点都在淮安城内。如果两个人都在他们生活的时期重修过这块碑的话,那更说明此碑之前就有已损之碑,并在原址重立。因损而修,几次更迭。且府市口的“学名”就叫“淮阴市口”。若简单表述,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官员,为淮安城内的“淮阴市口”几次修复了“淮阴市”碑。类似的事情,历史上在淮安城内最平常不过。“淮阴市”碑并不是名碑名刻,若与淮安城没有联系,不管是淮安人王廷器还是山东人刘大文,重修它为何?所以“移立”之说不足为信。
文革时期被红卫兵砸断的“淮阴市碑”
第三,勺湖公园中的“淮阴市”残碑是“文革”时期砸断的,并非是封建时期,且“淮安府又仿制一块立于城内”,纯属臆造。在淮安区北门大街与东门大街之间道路未拓宽前,此碑东西朝向贴于上坂街北首西侧潘干臣家附属房的东山墙,有碑楼,外观类似土地庙,南侧是潘干臣家正房北山墙。据说如此立碑方式,是因为过去碑立于十字路口时,因靠近漕运总督署、淮安府署,向北还有大河卫指挥使司等官衙,淮安城内大小官员行走到此落轿下马极为不便,便被一任知府改为贴墙立放,此后进出“不必多礼”。1968年文革时期,“淮阴市”碑被认定为“四旧”之物,先是由红卫兵用黄纸封盖,后被砸毁运走,放于城北大队市河边作为水码头的垫脚石之用,直至1987年北门大街拓宽时,才找回此碑残体。根据清晰可辨的残文断字以及碑后的“韩信故里”字样,遂知此碑厚重的历史价值。后妥善保存于勺湖碑林之中,供后人怀古瞻仰,并在府市口原碑旧址西北30米处仿照明代原貌复建“淮阴市”碑供后人访古怀旧。
阅读 1804